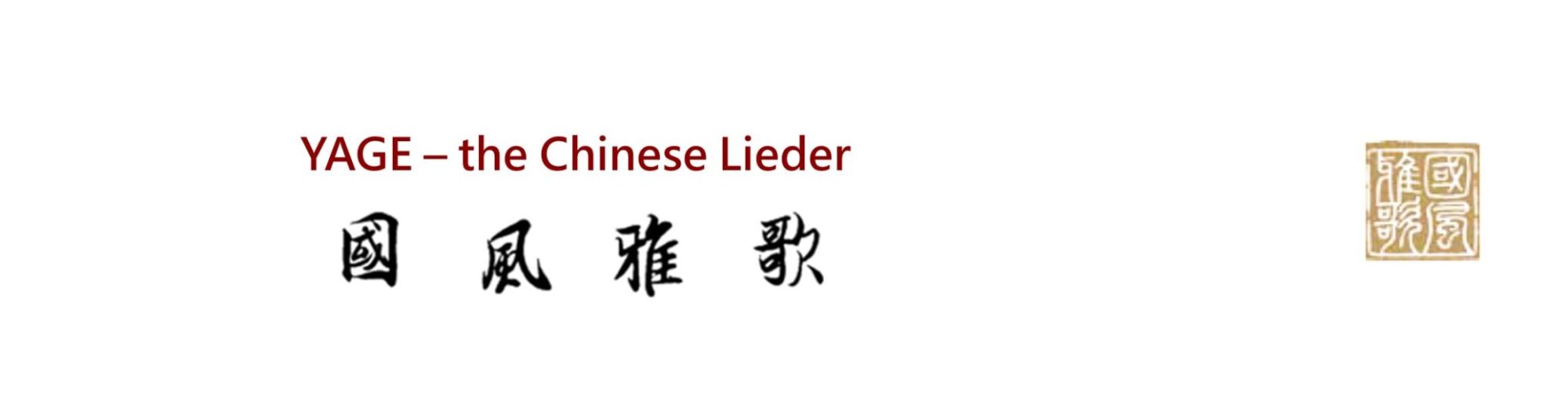范竞马: 让雅歌走向世界
作者: 李悦
范竞马生于重庆,从小跟随父母在四川凉山乡下长大。在身为老师的父母的熏陶下,范竞马从小就与艺术结缘,习提琴、学绘画,更受家中老唱片的影响,崇拜并模仿意大利美声宗师卡鲁索与吉利的歌唱。
与在特殊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一样,范竞马人生的转折点是1977年的高考。那一年,他在报考志愿里写下了四川音乐学院。就这样,范竞马成为那年唯一被四川音乐学院在西昌地区录取的学生。
1984年,范竞马以美声唱法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并从众多参赛歌手中脱颖而出荣获第二名,这只被誉为“凉山里飞出的金凤凰”刹时名扬全国。同年,范竞马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沈湘,并在老师的引领下,获得了英国“卡迪夫世界声乐比赛”水晶杯奖(男声组第一名),这次比赛,更是让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留下了这样的赞誉:“近十年来,欧洲罕见的男高音。”
此后,美国纽约罗萨·庞赛尔国际声乐比赛银牌奖、美国纽约歌剧精粹声乐比赛第一名、意大利卡罗·贝尔贡齐威尔第学院奖、美国费城帕瓦洛蒂国际声乐比赛决赛奖的获奖证书上,都留下了一个中国歌者的名字——范竞马。
范竞马的艺术道路似乎走得很顺利,但在范竞马的心底却始终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愿望——到罗马去,到意大利歌剧的发源地去学习声乐。
1988年,范竞马离开祖国,来到梦寐以求的意大利。他没想到的是,与祖国这一别,竟是15年。
翻开范竞马这15年的履历:1989年至1990年,师从意大利男高音贝尔冈齐;1990年应邀在美国罗德岛国际音乐节举办独唱音乐会;随后到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师从费罗;1993年,被意大利“男高音王子”科莱里收为弟子,唱遍世界各大歌剧院,与众多世界著名歌唱家搭档,无数观众为之倾倒,收获好评如潮……这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一帆风顺,但当回忆起当年的那些日子,范竞马却说:“真的没办法用语言去描述当时那段生活的感受。”
那是一段超乎常人想象的艰辛与磨难。在意大利名牌鞋店为人清点皮鞋,在纽约时代广场为行人画肖像,最窘迫的时候,他甚至一文不名。跑遍了曼哈顿上城和下城的所有教堂,只为寻找一个唱歌的机会……他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的是维持在茱莉亚音乐学院的进修课程。他受到过不同人的帮助,也曾遭到过背弃,他有过多次的希望与等待,也经历过同样多的挫折和失望,有时甚至感到绝望,但却又绝处逢生。然而,无论做什么,他始终没有放弃歌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继续歌唱。
记者:现在回头看,国外那段羁旅漂泊的经历对你之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范竞马:那段经历让我从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变成一个平和的人。也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不健康,习惯躲在角落里观察大家的一举一动,而我周围的人却可以毫无顾忌地想说就说,想拥抱就拥抱,想接吻就接吻。我意识到这对我的职业很不利,我决定改变。于是开始有意识地打开自己,展开微笑,主动跟别人交流,主动拥抱他人。有一段时间,我逼迫自己每天打几十个电话给别人,通过聊天,锻炼与人沟通的能力。虽然很难,但我做到了。
我小时候读《荷马史诗》,曾经幻想过罗马斗兽场的宏伟庞大。当我有一天在空中真正看到罗马斗兽场的时候,心情是失落的,在我心中矗立的那座宏伟建筑竟然是如此渺小。也让我第一次从这样的视角审视自己,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终于把自己的位置放对了,开始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慢慢我的事业也改变了。
记者:经历那么多艰辛与磨难,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一直没有放弃歌唱?
范竞马: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会说是理想,但后来我发现是一种倾向性。倾向性的涵盖范围比理想更大。如果心中有某种倾向性,哪怕是朦朦胧胧的,你也会不知不觉地朝那个方向走。我从小喜欢美声,正是因为这样的倾向性,把我带到了美声的发源地去学习。之后经历的辉煌也好,落魄也好,都是自己的选择。
记者:有没有那么一刻,突然有了成功的感觉?
范竞马:要看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成功。1996年,我在法国演了六部歌剧,还拍了一部电影,因此四处曝光。当时脑子里曾经闪过一丝念头,这难道就是成功的感觉?但很快,当我离开一年再回到法国时,已经没人再认识我了。我在想,这是多么的可笑,自己原本想象的成功,是多么的没有意义。
对我来说,当年从农村生产队到了县文工团,然后又考到地区文工团,再考上四川音乐学院到了省府,最后来到北京一直走向世界,如果这个漫长的经历算成功的话,那我应该是成功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偶然,之后我们才赋予它意义,而生命本身就非常神奇和有意义。离开生命本身追求成功,就像是在追求一个虚幻的泡影。所以,自己不要去考虑成功的事情,更不要去追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们只需要在职业范围内,尽量做一些自己认为是在精神层面上对社会有用的事。
记者:你似乎不太喜欢包装自己,很排斥商业化吗?
范竞马:并不排斥。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时代,无法脱离商业的环境、色彩、气味。但我从没想过走商业化道路。我相信歌唱是生命的一种冲动,是最本真的感情流露,也是更深层次上的情感表达。对于一个真正的歌唱家来说,歌唱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命的需要。市场、包装、炒作……本应是商人们的事情,真正的艺术家不会被卷入世俗的名利争斗和所谓的商业风暴。
记者:你觉得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范竞马:一定要拥有一颗纯净平和的心,没有私心,不为物质所惑。艺术家可以幼稚,但必须拥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艺术是纯精神创造的领域,学艺术要有奉献精神,要从精神世界热爱你所学习的专业,说到歌唱艺术家,需要对音乐有超越浮名功利的深刻诚挚。
记者:你曾说国外那段经历给你最大的感受是孤独,孤独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范竞马:我从8岁学会了独立面对生活。虽然我知道朋友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但一遇到困难先是自己去处理。
我喜欢独自徒步旅行,一个人在安静的时候,才会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独是好事,让你重新审视和回归自我。一个健全的艺术家应该学会享受孤独。
探索者范竞马:用美声唱中国歌曲
2002年底,范竞马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兴奋与激动之后,他逐渐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自己在国外唱了15年的美声,学了那么多外语,却很少用自己的母语演唱中国的艺术歌曲。“为什么‘茉莉花’被普契尼一改编就可以唱响全世界?可中国那么多民歌外国人只是‘欣赏’地听听,却永远不会跟着唱?”范竞马认为,无论是中国古典还是近现代诗词,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如果将它们与西方演唱音乐技巧完美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打造出具有世界水准的中国艺术歌曲。范竞马感觉到自己有一份责任,为中国艺术歌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于是,从2002年到2004年,范竞马连续出演了四部中国新歌剧:郭文景的《夜宴》、《狂人日记》,许舒亚的《太平湖的记忆》以及金湘的《杨贵妃》。在中国原创歌剧和用美声唱法演唱京剧等领域,范竞马做着一次次大胆的尝试。
2008年,范竞马录制了一张新专辑——《我住长江头》,曲目的选择从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到中国现代创作歌曲,从新疆、内蒙古民歌到云南民歌,穿越古今,纵横南北。“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被范竞马用轻言细语舒缓悠扬的歌唱方式演绎出来,听上去如苍茫暮色中揉动的琴弦。
然而对范竞马来说,演唱的内容并不是重点,重要是对歌唱方式的探索。范竞马说,他不希望外国人听到中国的民歌后,只是用“very interesting”来形容,之后就没有了下文。他想打破中国民歌的地域界限,对它们进行文化审美层次上的过滤,然后用国际通用的语汇与之嫁接,提炼创造出一种既有本民族自身文化特征,又能被西方接受和认可的国际性语言的艺术表达形式,在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输出我们民族自古就有的高雅情趣和人文情怀。
“我们要有自己的艺术歌曲,让外国人吟唱我们的古曲《阳关三叠》,就像我们哼唱舒伯特的《小夜曲》那样轻松。”范竞马说他现在做的“雅歌”就是这样一种探索尝试,他希望搭建一个平台,建立规范的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机制。虽然说这个平台搭建起来是个不小的工程,或许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想到是件具有传承意义的事,范竞马很欣慰。
记者:对你来说,音乐意味着什么?
范竞马:高级舒心的音乐就像是一种营养,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带来心灵的慰藉和快乐。吃好喝好是满足人的生理需求,欣赏古典音乐,对生活作出理性的思考,是我们作为一个健全文明人的必须。古典音乐不需要你听懂,感受就好。你或许不知道,古典音乐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激发我们天性中作为人固有的崇高感,帮助我们发现内心对于美的敏锐和追求。
但在如今这样一个商业社会,我们对音乐的重视程度并不够,音乐对人类的积极意义有时甚至被忽略掉了,很多人将音乐局限在娱乐的层面,只把它当做一种单纯的娱乐行为,这太遗憾了。
记者:一直做古典音乐,你平时会去听流行乐吗?
范竞马:会。流行音乐是必要的,是大多数人需要的。但是,流行音乐更倾向于娱乐消遣范畴。我们更需要一种高级的、有传统文化根基的音乐。
记者:你做中国的艺术歌曲“雅歌”,源于怎样的思考?
范竞马:我演唱了20多年的西方歌剧,总感觉缺点什么。后来我发现,这个缺憾就是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具有文学诗歌价值的、能代表中国人文思考和美学价值观的中国艺术歌曲,也没有这样一种演唱体系和规格。
现今世界上几大公认的演唱流派,如意大利的美声(Belcanto),德国的艺术歌曲(Lieder),法国的歌唱诗(Chanson,也叫Mélodie), 还有俄罗斯的浪漫曲(Romance),它们之所以能够各成体系,同时又能超越民族的边界被全世界接受,就是因为实现了各自不同的语言特征与统一的美声技巧的完美结合。
中国也应该有这种既具有独特民族文化特征,同时又能被世界认可接受的艺术表达形式,我想到了我们的唐诗宋词,它们本身就极富音乐性。虽然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但我们可以凭借我们的想象力,用歌声来完成诗词背后的延伸。也就是说,除了几大国际公认的声乐演唱类别之外,我要创立一种新的歌唱形式,就是中国的“雅歌”。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就已经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像赵元任这样的国学大师,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搭建一个研究、培养、创作中国“雅歌”的平台。
记者:搭建这个平台的过程难吗?
范竞马: 难。我从2008年开始考虑做这件事,现在只能说有了些眉目,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最终这个平台还没有搭建起来。很多人以为,雅歌是用美声唱中国歌,其实不是,我们必须先从建立培养机制开始,从中文吐字、规格、训练到与美声技术的嫁接,是一个系统工程。
这件事的进程可能会很艰难,但总要有人去做这种奠基工作。
记者:但是中国老百姓似乎对美声唱法不太接受?
范竞马:我们的民歌元素从旋律到音乐结构都非常好,用美声唱法是没有理由不能唱的。老百姓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我们在演唱中忽略了自己的母语。任何一个民族的唱法,都是和本民族语言的发声方式密切相关。我们现在很多人以为大音量、宽音域、唱得响就是美声,其实不是。我们必须寻找到符合汉语语言标准的中国式唱法。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艺术歌曲的未来?
范竞马:充满希望。我发现在国内关注古典音乐的年龄段要比西方低得多,在古典音乐会现场,很容易就能看到80后的观众,这在国外是不可能的。我在国外的fans都是老年人,中年人都不多,但在国内,我有很多80后的fans。年轻人越喜欢,我就越感动。我相信,经历了物质膨胀的年代之后,我们总会静下心来,慢慢体会一些精致的、从容的艺术。艺术应是生活的一部分。也许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家庭的聚会,将不仅仅是吃饭、喝酒、唱卡拉OK,而是会在自己的家中举办小型音乐会上,演唱艺术歌曲。
我看好“雅歌”的未来,尤其是两个月前在清华大学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120周年的音乐会上,我演唱了赵元任先生谱写的艺术歌曲,发现无论年轻人还是老教授都接受并喜欢这种艺术形式,这给了我信心。对中国艺术歌曲,我永远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