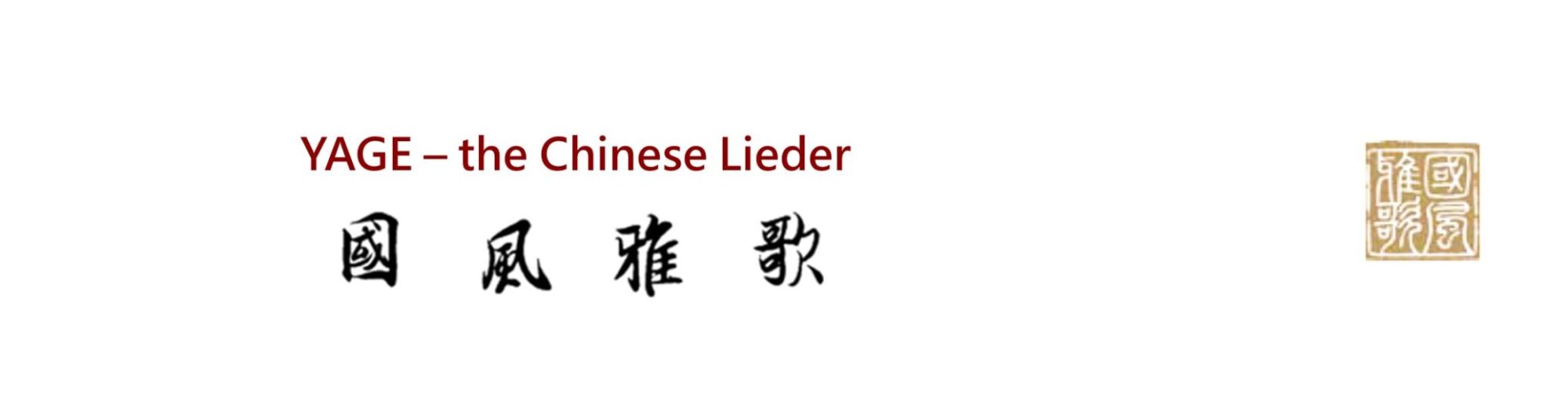美丽星期天”大众乐评 之《塔尖上的范竞马》
2014-3-13 09:26 AM 分类:大家评乐 作者:王芳
1.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大家觉得咏叹调、HIGH C音很难吧?错了,咏叹调和HIGH C最容易唱,反而,艺术歌曲才最难把握。”这个春荫如雾的周日午后,在深圳“美丽星期天”“中国雅歌行”公益演出现场,范竞马不无幽默地和观众展开了轻松的交流,不少观众会心哑然。此种言辞,由这位全球歌剧界星光熠熠的著名华人男高音口中道出,便自然拥有一种掷地有声的力度。专业语境中,艺术歌曲对歌者艺术造诣、艺术感觉、演唱技巧全方位的挑战,的确是音乐界通识之一。
旨意全球艺术歌曲的“第五种流派”,范竞马和他的伙伴们所创的“中国雅歌”无疑属于融汇中国文人和西洋室内乐两种传统的新生事物。诗歌吟唱在中国可以追溯至《诗经》“风雅”吟唱,“颂”更可配合黄钟大吕;初唐以降,雅与歌分道扬飙,成为彼此相互依存却又泾渭分明的“花开两朵”。雅,越来越多以文人创作与状态为呈现,以诗骚辞赋创作为形式表达;而歌,自初唐“渭城朝雨邑轻尘”的艳惊四座开始,乃至井水间传唱的“柳词”,“歌”只是职业歌妓的事。自唐而宋,而明清,之于愈发纤弱的文人中国,诗文堪为经世大业,歌戏均属倡优小技(除唐明皇、宋徵宗等极少数派例外),这也是中国史上歌、戏大家屈指可数的根本缘由。
于是,“中国雅歌”溯本追源只能至清末民初,追溯到那场战争意外的副产品:为古老而顽固的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之门,让东方和西方重新拥有流畅的沟通路径。东方之“文雅”触碰西方之“艺术”,出了以赵元任、刘半农等为典型的融东西文化菁华于一身的名宿。这一群凌云志士的文化引领者们,在东西方文化的剧烈撞击间从胸怀中华到环球之“天下”, 迸发出创造力无限,他们不仅忘我地投身创作,更身体力行,唱念做打无不尽之极,兼携时任中国最高学府教授之利器,改风易俗,致使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无不生机勃发,中国近代文明的天空群星璀灿,仪容妙漫,时代风骨令无数当下人神往、动容、追逐。而“雅”和“歌”,也正是此时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范竞马先生正在创造并推崇“中国雅歌”,正在传承、重塑、宏扬此种可称为“歌雅同体”的近代传统。
然而在中国当前文化总体态势“下流化”、娱乐化,K歌当道、雅意稀缺的网游时代,这一站立金字塔尖的小众“雅歌”事业,坚持与推动之难可想而之。
2.
艺术歌曲,耳熟能详的曲目有舒曼、舒伯特的《云雀》、《小夜曲》等,在艺术范式里甚爱优美与浪漫的爱乐者,对艺术歌曲自然会有先天的亲近。
我更想说另一个层面的切身体会。虽然艺术无国界,但正如“桔生淮南而为桔,生淮北而为枳”,在我剧场看音乐剧《猫》时,饶是《MEMORY》响起,美则美矣,看着台上金发碧眼的演员,耳中听着英语,我却从心底升腾起些许陌生与隔离感。能探知其美,这种美的观感却无法融入我的血液和细胞,无法让我身心彻底沸腾——这是我成人后在持续的艺术欣赏经验里的切身之感,我称之为基于理智、学识与基于根脉、自性欣赏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当然必须承认,在古典音乐、西方文化熟知、外语等基本能力上,我还不具备能够全身心投入“完全欣赏”状态的能力,我的欣赏常常处于“学理化”欣赏,这种欣赏自有其美好,然而却无法让我全身心融入,我称这种在艺术欣赏上的局限为“有我”之境。然而当范竞马和他的弦乐四重奏以及钢琴联袂奏响《渔光曲》,“云儿飘在海空”唱句初出,我已觉身心全部已渐渐融化在空灵、摇荡的叹咏之间:我仿佛便已化身波光麟麟的湖水,便是那晨光里跳跃的鱼,便是“轻撒网、紧拉绳”的打渔人……“烟雾里辛苦等鱼踪”,歌唱和弦乐行进的优美间蕴涵飘散着淡淡的忧伤,和我们儿时读的“对影成三人……我歌你且和”、和红楼潇湘馆里的春愁、和阳关三叠、渔舟唱晚、和寒山寺上的暮鼓晨钟一脉相承,那种沉醉而迷人的空灵,让我心襟摇动,无法自已。
我如此解释:西方的艺术,因为于我的“他者性”,结果是我在欣赏中只能到达“有我”之境;而纯粹东方的“中国雅歌”,卿本同根,血脉相连,声声倾诉、句句叹咏都无比精准地击中我成长中所经历的美与忧伤,这种文化情绪上的持续共鸣,将我引入无数个我重叠的幻境。音乐会上范竞马且歌且言:在“雅歌”艺术形态上,他希望追寻纯粹、更纯粹的表达;此种纯而又纯的凝练、过滤,经由有序振动的空气粒子和文化共振,在听者耳里、心中凝结成优美而忧伤的“忘我”共鸣。我认为范竞马在这首歌技艺上追求一种“空的极致”效果,声音从共鸣腔出来,向着天空伸展。某个瞬间,我体会到歌者在演唱间“天人合一”的通透与浑然。
3.
在“雅歌”音乐会全程,范竞马和他年轻的伙伴们从声音、技法、到肢体语言,都充分体现出一个“雅”字。雅者,儒家所言“温柔敦厚”也。我以前有个认识误区,以为歌唱家必须站着才能唱,而范竞马先生却颇令人意外地坐着完成了他这场深圳公益场绝大部分歌曲的演唱。他说,因为我不想大家把焦点注目在我一个人,因为“中国雅歌”音乐形态的定义便是观众眼中“室内乐+人声”的团队表现组合,从邹野老师的创作编曲开始,到四重奏+钢琴+人声之间彼此烘托、互相温暖、各种丰富而细腻的细节,当然,他的坐姿丝毫无损歌声穿透心灵的力量。作为公益场,全免票的深圳观众也让人叹为观止,除了个别时间孩童喧声和偶尔手机响起,绝大多数人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跟随范竞马老师流连在雅歌的优美间,沐浴这段音乐的春光。
现场范竞马有几个温暖的花絮。观众未及乐声全止便热烈鼓掌,他极平和地娓娓规劝,“我不批评,但不鼓励。因为掌声会打断艺术家们的专润。”听到现场主持人持唛音量过大,他忍不住一反绅士常态,拿过话筒说道:“在音乐厅用唛,应该保持这样大小的音量。声音太大,正是咱们国人浮躁的表现之一。”又说:“用这个音量说的话,你们如果希望听清楚,就会认真、用心倾听,就能聚精汇神。”的确,雅歌的倾听只有在凝神定气后方能心领神会,“花飞花,雾飞雾,夜半来 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正是春花处处、流云飞雨的时节,在“雅歌”的如泣如诉中会于心而动于情,你的嘴角浮起蒙娜丽莎的微笑,或者不知不觉,泪已满腮。
音量大小,直接关乎艺术的表现力。艺术的至境,公认为擅长约束与留白,擅长深入而浅出。艺术的至境,更是“厚”之后的“薄”,是丰瘐尾随的轻盈,是经由技艺上“度”的把握抵达表现力高峰的“曲终人不散,江上数峰青”。歌者极致的追求,便是席间听者身心的无尚应和。
我想,雅歌,是范竞马在登临歌唱艺术高峰后选择再一次出发的新挑战,又一株在阳光下静谧开放待采摘的雪莲花。虽然雅歌在中国必然是小众、又小众的艺术,“歌者如朝露,但伤雅者稀”,然而艺术之美不能全民公投,引领和培育是前行者不可懈怠的责任。于此,我十分乐意于见到范竞马和他的伙伴们在闪光的塔尖上,以雅歌的纯粹与挚着,让中国艺术这座已过度沙化的金字塔渐渐恢复坚石壁立。